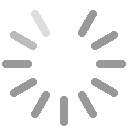
《林泉高致》原文及译文(六)
中国美网·26851 浏览·2018-06-06 11:04:17
【原文】
柳子厚〔1〕善论为文,余以为不止于文。万事有诀,尽当如是,况于画乎!何以言之?凡一景之画,不以大小多少,必须注精以一之〔2〕。不精则神不专,必神与俱成之。神不与俱成,则精不明;必严重以肃之〔3〕,不严则思不深;必恪勤4以周之,不恪则景不完。故积惰气而强〔5〕之者,其迹软懦而不决,此不注精之病也;积昏气而汨〔6〕之者,其状黯猥而不爽〔7〕,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;以轻心掉之〔8〕者,其形脱略而不圆〔9〕,此不严重之弊也;以慢心忽之者,其体疏率而不齐,此不恪勤之弊也。故不决〔10〕则失分解法〔11〕,不爽则失潇洒法,不圆则失体裁法,不齐则失紧慢法,此最作者之大病出,然可与明者道。

【注释】
〔1〕柳子厚:柳宗元,字子厚,河东(现在山西运城永济一带)人,唐宋八大家之一,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和思想家。世称“柳河东”,因官终柳州刺史,又称柳柳州。
〔2〕注精以一之:指集中精力,专心一致。
〔3〕严重以肃之:严肃庄重地对待。
〔4〕格勤:恭敬勤恳。格,恭敬,谨慎。
〔5〕强:勉强去做。
〔6〕汩:扰乱,搅浑。
〔7〕黯猥而不爽:黯,暗淡无光。猥,杂乱不堪。爽,畅快。黯猥而不爽,指下笔作画黯淡杂乱而不明快。
〔8〕轻心掉之:“义同掉以轻心”。指用轻率的态度来对待。出自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:“故吾每为文章,未尝敢以轻心掉之”。
〔9〕脱略而不圆:(形态)散漫简陋而不周整。圆,周整,周到。
〔10〕决:果断。
〔11〕失分解法:分解,指条理分明层次清晰。法,法度。失去了条理分明层次清晰的法度,意指笔法上不够清晰明快。此后“失潇洒法”“失紧慢法”也作同样解,意思就是风格上不潇洒、规章上不完整、布局上未兼顾轻重。

【译文】
柳宗元善于议论文章写作,我认为不只是文章写作,做任何事情都有诀窍,都应当像柳宗元说的那样,更何况是作画呢!为什么这么说?创作任何一幅画,不管它尺寸大小,内容多少,都必须精神专注一致地对待。若不精神专注,就会心神不一,必须要聚精会神地去体验,否则便会精力不清明。必须要严肃庄重地对待它,否则就会导致思虑不深。必须要恭谨勤勉地完成它,否则景象便不能完备。所以,因懒惰之气的积累而勉强作画的,笔迹就会瘫软怯懦而不果决,这是犯了不精神专注的毛病。因昏聩之气的积累而乱画一通的,往往形状黯淡纷杂而不明快,这是不能聚精会神的弊端。轻率对待作画的人,笔下形态就会散漫简陋而不周整,这是未能严肃郑重的弊端。以轻慢之心疏忽对待的人,他的画就会简陋草率而不整饬,这是未能恭谨勤勉的弊端。所以,不果决就会在笔法上不够清晰明快,不明快就会在风格上不够清爽流畅,不周到就会使整幅画章法规制有欠完整,不整齐就会使布局轻重失当。这些都是画家们最容易犯的毛病,但是只能跟明智之人谈论。

【原文】
思〔1〕平昔〔2〕见先子作一二图,有一时委〔3〕下不顾,动经一二十日不向〔4〕,再三体之,是意不欲。意不欲者,岂非所谓惰气者乎!又每乘兴得意而作,则万事俱忘,及事汨志挠〔5〕,外物有一,则亦委而不顾。委而不顾者,岂非所谓昏气者乎!凡落笔之日,必明窗净几,焚香左右,精笔妙墨,盥手涤砚〔6〕,如迓〔7〕大宾,必神闲意定,然后为之,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掉之者乎!已营之,又撤之〔8〕;已增之,又润之;一之可矣,又再之;再之可矣,又复之;每一图,必重复终始,如戒严敌,然后竟,此岂非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!所谓天下之事,不论大小,例须如此,而后有成。先子向〔9〕思,每丁宁委曲〔10〕论及于此,岂非教思终身奉之以为进修之道耶!

【注释】
〔1〕思:指郭熙之子郭思。这一段是郭思的评注,所以自称“恩”。下文亦然。
〔2〕平昔:过去,往常。
〔3〕委:搁置。
〔4〕不向:不作画。
〔5〕事汩志挠:事情或精神被扰乱。
〔6〕盥手涤砚:洗手和砚台。盥、涤都是洗的意思。
〔7〕迓:迎接。
〔8〕营:开始作画。撤:停止作画。
〔9〕向:对着。
〔10〕丁宁委曲:丁宁,通“叮咛”,叮嘱意。委曲,把一件事情的原委和过程讲出来。

【译文】
我以前看父亲作画,有时候丢下画不管,动辄一二十天不闻不问。我反复体会其中的原委,这是因为他不想动笔的缘故吧。而不想动笔,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惰气使然吗?有时候他又会兴致大发,志得意满地画起来,以至把别的事都忘在脑后。等到事情不顺心志烦乱,哪怕有一件事干扰了他,便又会丢下画不管。丢下不管这种行为,难道不是所谓的昏聩之气使然吗?但凡执笔作画之日,必须让窗户保持敞亮,把桌子打扫干净,身边焚上香,备好上佳的笔墨,洗手,洗砚,就像是要迎接贵宾一样,必须要心神闲适安定之后才能动笔,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不敢轻率对待吗?画画停停,增增改改,一遍可以了,还要再来一遍;两遍还不够,又多来一遍。每张画都必须从头到尾反复修改,如临大敌,如履薄冰,这之后才算完,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不敢以轻慢的心来忽视它吗?天下的事情,无论大小,按例都应当如此,才能有所成就。先父每当对我嘱咐告诫说到这些,难道不就是要教我终身奉行这个道理,来作为自己的进德修业之路吗?

【延伸阅读】
关于文中所论及的为画“四法”,历来大家多有不同的解读。陈传席先生在其《中国山水画史》中将“四法”中的“分解法”解释为:“‘分解’即用清水把浓墨分解成不同层次,如‘墨分五色’然。分解法则指墨色的深浅层次、浓淡干湿的恰当配合以及清晰度的掌握方法”;将“潇洒法”解释为:“使画面清丽明朗的方法,这是要画家挥洒自如才能达到的”;将“体裁法”解释为:“‘体裁’在这里指选择完美的山水境界,以能体现出林泉高致”;将“紧慢法”解释为:“这里的‘紧慢’,用今天语言表达即‘大胆落笔,小心收拾’,‘紧慢法’重点在小心收拾,在作品的最后润饰。”相比之下,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在其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中将“四法”解释为 :“分解法,殆指笔墨的浅深轻重而言。潇洒法,殆指笔墨之挥洒自如而言。体裁法,殆指形体之完备而言。紧慢法,指最后之修润而言。”而在文中,郭思对这“四法”的阐释则是他本人提出的“两气两心”:“惰气”“昏气”“轻心”“慢心”。身负父亲郭熙的亲传,郭思对“四法”的阐释也许最能得其中真髓,而后人对“四法”的理解,最终也只能从这八个字中窥见一斑。

【名家杂论】
文中说“柳子厚善论为文”,并以文和画相类比阐明“万物有决”的道理。那么,传说中的柳宗元又是怎么讲文章的?
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,柳宗元和韩愈一道领导了古文运动,完成了文体改革,自然其创作的一大部分必然少不了文论。柳宗元对文章的看法很大一部分可以用古文运动的“主流”观点来代表: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道并重”、“崇尚儒家”、“经世致用”等。具体来说,柳宗元的“道”比韩愈的“道”更接地气。他在《送徐从事北游序》中说:“以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之道,施于事,及于物。”由这句话可以看出,他所谓的道,不是柏拉图式的高居于云端的道,而是“及物之道”。他所言“文以明道”,就是说文学是为了阐明或宣传“施事”“及物”“辅时”——即有补于社会现实的“道”。
由柳宗元的文论来关照中国画的画论,其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《林泉高致》中的论点,强调“注精以一”,强调“神与俱成”,强调“恪勤以周”。总而言之,就是要恭谨严肃地进行创作。事实上自魏晋以来,许多文艺创造讲究的是潇洒和雅趣,是脱略之美而非严谨之妙,是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,而非“精研章句,训诂文字”,更有甚者,崇尚的是天赋秉性,而非后天修德。这样一个“任性”的才性论色彩装点的时代特色,在诗文方面历经了唐代古文运动,已然变得肃穆许多,而书画则要到宋代才变得更加强调“规矩”。郭熙身在宫廷画院,处事低调严谨大概是一种习惯,但这种习惯反映到他的艺术创作中却成为了一时之风气,使得作画成为一种细致的手艺活,必须勤学苦练才得其中奥妙。
克勤克俭的原因是什么呢?自然是因为在他看来,作画本身并非一时情绪的宣泄,也不仅是个人心灵的具现化,而是要创造出一个工巧的境界出来,可以供人寄托心灵恍然如梦,可以供人行走仰望居住游玩,可以“有益于世”。这样的作品,怎么能够仅凭才华而随意涂鸦呢?可以说,从柳宗元的文论到郭熙的画论,其中对于艺术的态度,对于创作方法的立场,始终是一脉相承的。另外,原文中提到的“惰气”“昏气”“轻心”“慢心”,也同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提到的“轻心”“怠心”“昏气”“矜气”惊人暗合:“吾每为文章,未尝敢以轻心掉之,惧其剽而不留也;未尝敢以怠心易之,惧其弛而不言也;未尝敢以昏气出之,惧其昧没而杂也;未尝敢以矜气作之,惧其偃蹇而骄也。”两段话一比较,可见其中神似。
除了柳宗元的影响,郭熙画论的宗旨,其实和当时整个宋朝社会正在慢慢成型的理学风气是相合的。朱良志先生在其著作《扁舟一叶》中认为,郭熙这一段论述几乎全依二程(程颢和程颐)的思想立论,其秉承理学(新儒学)涵养心性,提倡一个“敬”字思想,正来源于二程之“主敬说”,认为理学是郭熙的核心思想。不过与其说郭熙是师从了理学的思想,不如说他的理念和两位同时代的大儒有“琴瑟和鸣”之妙。儒学是宋代的显学。儒学复兴也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。在神宗时代,二程学派和理学形成。它与汉唐儒学不同,更强调个人,以及主体精神的高扬,突出“格物致知”“去欲存理”的重要性,把道德修养抬到极高的地位,是儒释道三种不同的宗教形态进一步融合的产物。儒释道“三家店”思想经过长期的争执和交融,最终还是走向了统一,从而促进了宋代新型哲学的产生。
由此也不难理解,为何前半生专心于修道的郭熙,会在晚年告诫子嗣要以儒学为宗,其实儒也好,道也好,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下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——或许可以把他叫作宋代的“中国特色”。